抱歉,开篇要刺大家的眼。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魔幻现实什么样?
《梦华录》这一幕多少诠释了。
浮华、刺目、矛盾、诡异。
赵盼儿终于开了酒楼。
不曾以色事人的三个女老板,请了一堆乐籍女子,吹弹唱跳,以色事人。
谈笑间,宾主尽欢。
可以说,它是这部有“梦华”而无“录”的古偶剧,最现实的一幕。
足以载入国剧的“风尘史”。
良家老板,乐籍女子。
她与她们的区别是什么?
是什么使她买她们跳?
她们跳得不好,会有人安排她们去学习管账吗?
她们都从哪里来?跳过了多少场?会跳到何年何月?
在这部古偶,或者一句“她是女主,她们不是”就可以轻松带过了。
她们,也不会再被看见。
但其实,曾经我们的影视剧,一直都有看见她们。
她们的脸。
也曾被认真、理解、深情、以血以泪地好好刻画过。
今天飘想来回忆下。
那群,风尘女子。
笑脸
动起笔发现,风尘女子这个关乎血泪的名词,其实长着一张笑脸。
美不美,脑中闪过的先是笑。
不论想不想笑。
笑脸卖多了,笑贱。
眼泪反升了值。
柳飘飘(张柏芝 饰)就是靠两滴假模假式的芥末泪,在一堆假模假式的笑脸里,成功赚了来找初恋感觉的龙少的钱。
她不忘给自己摇旗:我是真心爱你的!
电影《喜剧之王》
钞票抓在手,泪还挂在脸上,秒瞬换了一张笑脸。
同样是笑中带泪。
对比后来听到尹天仇(周星驰 饰)的“我养你啊”,不屑一哂后的大笑大哭。
她当时就想笑,但她不能。
她当时也想哭,她也不能。
不破的理已证:拍风尘女,拍“真心”,比拍“假意”难多了。
周予导演却偏偏爱拍“真”。
1981年,他的《杜十娘》。服化、文常、人物刻画、镜头耐品度都是逸品。
尾声高潮时,杜十娘(潘虹 饰)红裙如血,含泪问天。
一幅教科书式的“怒沉百宝箱”图画。
电影《杜十娘》
但,是什么让这画真正活起来了?
飘认为还是前头细节处的两次“真笑”。
第一次,在京城名妓杜十娘从良的新婚夜,她笑得非常幸福。
院门写着“杜媺”的花牌摘了,交杯酒喝过,新郎醉倒了,她缓缓撕破绣着“白眉神像”的手帕。
过去她们院中姐妹初一十五都要拜的,保佑自己的“孤老”(嫖客相好)不变心。
她看着新郎,神魂震颤地笑着:
不,你不是杜十娘的孤老,不是我的相好的,你是杜媺的……丈夫。
沦落风尘八年,直到今天,我才觉得自己,像个人了。
为这一天,她等得太久,绸缪了太多。
考量,测试,激将老鸨子三百两就肯放她从良,试出李甲有为她奔走的真情,她还是只拿出一百五十两,要再看看他有没有另外那一半的心。
终于她得以脱籍,伴君还乡。
十娘又一次真心地笑,就是对于作良人妇、埋街食井水的憧憬。
他说要带她回“家”。
周予导演在此处运用了一串高妙的交替闪回镜头。
十娘靠着爱人的肩,勾勒着家的样子。她说,我想咱们的家,一定是所极大的院子,门前有一对石狮子?
爱人脑中的画面,却是家中森严的朱门,诗礼传家四个大字如同四座大山。
一对石狮子捍卫着铁门槛。
十娘还是幸福地笑着,猜公婆的样子。
母亲是位菩萨心肠的老人,父亲嘛,像是蛮厉害,不过,他会喜欢我的。我一定能够让他喜欢我。
但她以为可托终身的男人,脑中闪回却是严父的威怒,心里早泻了底。
处处讲烟花女之笑。
却处处尽显烟花女之泪。
不吝篇幅体现了十娘的心智、聪明、与命运的抗争,包括财富与学识。
但,用意却不在彰显她的特殊。
而是哀叹她的不特殊。
以才之高,财之豪,反衬她微小愿望仍被吃人的时代啃食的残酷。
“我只想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但是……”
一笑过后,无限悲凉。
这一版杜十娘减少了许多传统戏曲颇有“爽感”的骂孙富,恨李郎的骂词。
改编戏份加在了十娘再度被卖,自杀前想到最初和母亲分离时。
在故地水乡,老鸨子买了她,她的母亲追出来,喊着她的名字,跳下了桥。
滔滔江水如时代奔流,不是具体的哪一个人,是它吞噬了她和她们。
哭脸
风尘的笑,要以泪书写。
因为要看见背后的哀绝。
那眼泪呢?
来看这两张脸。
电视剧《爱情宝典》之《救风尘》《卖油郎独占花魁》
是的,这是同样由乐珈彤饰演的两张脸:赵盼儿和瑶琴。
不同的是,盼儿哭,是因为百感交集。
好姐妹宋引章终于逃脱大难,自己也终于撮合了安秀才和她。
虽然改编版里,她对安秀才有眷恋。
但,她哭得颇自豪。
他们俩好就是我好了
这滴泪,正配霁月光风,敞敞亮亮一赵盼儿。
而瑶琴的泪,是哭苦尽甘来。
她像杜十娘一样骗了老鸨,把赎身的钱交给了爱郎。
一个穷苦,坚毅的卖油郎。
她等着他来娶她。
她知道他一定不会负她。
他也确实不会。
电视剧《爱情宝典》
有人说,瑶琴是幸运版的杜十娘。
但她所遭遇的,何尝不是人间至苦。
何谈幸运。
靖康之变后,本是官宦之女的她和爹娘在逃离汴京时走散。
被人贩子拐进青楼,反抗不成被强暴,只能被迫接客。
几年后遇到男主,才终于又燃起对生活的热情,对人心的信任。
与其说,她是幸运版杜十娘。
不如说,她和丈夫秦重(任泉 饰)是bg版“底层自救”的赵盼儿和宋引章。
来看“残花败柳”和“贩夫走卒”的对话。
你舍不得我死?比命还难舍。我已是残花败柳。人间世道,一个小女子怎么承担得了?我看小姐如明月,刚才的事更让我觉得小姐至纯至洁。
《爱情宝典》的高明处,在于花了几乎同样的笔墨,刻画卖油郎秦重的“苦”。
他同样也在这肮脏世道里打滚,被骗,被诬陷,被关,被捏揉搓扁。
这不是一个白璧无瑕的男主谈对女主“干净”或“不干净”的介不介意。
不是位高权重的人,对弱者的施舍。
不是幸运儿偏差带来的优越。
他和她就是苦海泥淖中,看到了彼此至纯至洁灵魂的两个人。
如同当初他攒了两年半的银子,才终于见到花魁,却心无杂念地照顾了她一夜。
在香艳矫俗的欢场地,为她唱着乡音歌谣,宽慰她的思乡情。
和她互诉心中苦水。
似乎是他救了她,但她也是他灰暗生活里,不可触及却无法不向往的光。
他们是底层的,渺小的,不特别的。
但,又是这样特别。
因为,他们如今已是“写不出”。
鬼脸
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
胭脂虎(李凌云 饰)有一张鬼脸。
鬼在可怖。
她是同喜院的老鸨子。
干瘦的躯干,顶着一颗瘦干的脑袋,人却油滑得很,像一只湿亮的大老鼠。
穷人家的姑娘佟大香(李萌 饰),刚被“介绍”到这里“找工作”时,她习以为常地慢悠悠问:“这人扎不扎手?”
得知大香家里只剩了个不知事的妈,她眼珠子滴溜溜地,像看见钱已进口袋了似的转。
这张脸,又鬼在多变。
大香刚被卖来这地方时,姑娘们鱼贯而入,胭脂虎问她们卖了几个铺(接了几个客)?
领头的一号说,我卖了六个。其余人说,只卖了一个。
她立刻一副笑模样对一号,你今儿多挂客,明个妈还给你包饺子呢。
骗大香下店卖身、以后有你的好日子过时,她笑得更开、更亲和。
咱们这是吃尽穿绝的地方,水来洗手,饭来张口,又不用你去干苦活。
要什么,给你买什么,不比你下工厂强得多么?
这种虚幻的“自由”,便是现在“要做便做那妓女”的向往源头。
妓女梦想家和姨太太女孩们,在虚假的勾勒里,大谈自己的“愿”与“不愿”。
但,大香就是不愿意的。
她拼了命地反抗过。
但胭脂虎把笑脸隐去,把鬼脸变过来,让“她男人”先去“破了她的身子”。
把大香强暴了。
自己再来做好人:不要脸,下店你嫌寒碜,背后勾引起我男人?我先不给你说出去,说出去你得羞死!
干脆,给我好好下店,这回算饶了你。
绑住大香的,不仅是院里的龟奴打手,压着的卖身契,还有院外无尽的绳索,人们“自由”的舆论。
谁还不能自由地去践踏一个“不要脸”的女人呢,你是贞洁烈女么?
你得羞死!
“寻常恩客,清秀公子,再幸运些遇着的动心的……”
梦想家们总觉得,自己潇洒做妓女,可以做得三六九等,区别对待。
但其实,区别对待是看她们赚的钱多钱少,而她们都是三六九等里的那个九。
天天卖铺吃饺子的摇钱树一号,得了性病,胭脂虎关心地给她治病。
拿着烧热的火钳子,直接往下身烫。
毒病就得毒治!
我见得多了,拿长剪刀直接剪!
一号就这么送了性命。
没有姓名,她只是卖铺最好的一号。
还剩下一口气,她微弱地叫着:妈,我还活着呢。
——这还能挣钱呢?!装上算了。
一号被活活钉死在棺材里。
她的“死活”不在于有没有一口气,而是在还有没有用,还能不能挣钱。
曾参加拯救教养妓女运动的张洁珣老人回忆,这都是她真实经历过的女性。
《电影传奇》
咚。咚。咚。
钉棺材声,在大香和姐妹们耳边响着。
她们都曾是大香,她们也将会是一号。
“早晚……咱们都一样……”
她们都哭着。
“鬼”把她们也变成了鬼。
人脸
鬼,是哪里来的?
人变的。
“胭脂虎”是一张鬼脸。
饰演她的李凌云同志,却是一个人,一个极具悲苦和先锋性的女人。
但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张脸,演员出演这一角色时,才不到30岁。
她曾是一个真正被迫害的风尘女性。
(19岁的李凌云和饱受摧残后的她)
李凌云自幼不知父母是谁,6岁落入老鸨子胖大奶奶手中,跟着又学了戏。
13岁出师,开始跑码头卖艺,19岁被人纳为五姨太。
22岁,再度沦落风尘,回到胖大奶奶处登台唱戏,同时做变相妓女。
抗战结束后,胖大奶奶干脆把她送入三等窑子“东合顺”,受尽凌辱。
直到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封闭妓院,改造妓女,李凌云和院里的其他妓女才被送入生产教养院。
而她出演“胭脂虎”一角的经历,也非常曲折,拍摄时,她曾数度哽咽。
不难看出,奉献了血泪表演,被真情实感的观众投石子的李凌云,才真正是片中的“佟大香们”。
是一个曾经被摧残为“鬼”,又终于由鬼变成“人”的女性。
这过程十分漫长,艰难。
像歌里唱的“千年的冰河开了冻”,哪怕得以实现,也要克服很多问题。
由于苦难、蒙昧、无知、贪财、缺乏信任、羞于治病等等原因,很多妓女都对改造有抵触情绪。
纪录片《荡涤尘埃》(2011年,主讲新中国成立后取缔妓院和解放妓女)
她们从开始排斥看病,到后来起个大早,蹦跳着做健康操。
从不事生产,甚至有人企图“勾引”“讨好”指导人员以逃避工作。
到脱去长袍短卦,穿上工人服。
她们意识到了“快捷”的“不快捷”。
去他的卖铺。
比就比谁打的纱团最快,最好。
她们的产品,是有牌子的。
叫做“新生牌”。
因为她们就是得到“新生”的一群人。
她们的劳作不仅真正实现自己养活自己,在全民图强的时代,她们也成为了建设新社会的一份子。
其实,真正的问题从来只有:
是不是把她们当成和自己一样平等人格的人对待。
鬼变人,人变鬼。
都并非自愿。
鬼变人的过程很漫长。
人变鬼的距离却很近。
鬼变人,是从来只能托命于求签打卦的如花,在十二少送上“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时,脸上的神采。
她以为她可以。
人变鬼,是菊仙那一瞬灰败了的眼光。
她也以为她可以。
鬼变人,是刘姥姥一把扯下巧姐头上的艳红花朵。
母亲的一点恩泽,姥姥的得施知报,让她可以逃出火坑。
人变鬼,是“难为她一片痴心”的杨九红,也曾娇艳有光,策马闯关,也曾真实地反抗过,却因为身份,不能戴孝、不被承认、不被尊重、不能哺育亲儿……
最终选择把这一切悲剧重演,变态偏执地报复在自己女儿身上。
鬼想变人,是宋引章千方百计,时时刻刻念着的“脱籍”愿望。
人要变鬼,却是一句轻飘、滑稽的“脱籍脑”指责。
因为轻飘地描绘着她们的苦难。
所以歇斯底里的“我想脱籍”放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
变成了滑稽的不知好歹,没事找事,太烦了,祥林嫂吧你。
不谈泪,无以谈笑。
不谈浊,无以谈洁。
不曾真正地看见苦难,承认苦难,反抗和挣脱枷锁的口号,也将苍白无力。
不是从心里站在一起。
又怎么去谈“站起来”。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每日简讯:港股低开,恒生科
每日简讯:港股低开,恒生科  全力以赴稳住基本盘 外贸高
全力以赴稳住基本盘 外贸高  “大筒仓”元宇宙空间项目特
“大筒仓”元宇宙空间项目特  最新快讯!税友股份也踩雷五
最新快讯!税友股份也踩雷五  “猪王”牧原股份涉嫌虚增利
“猪王”牧原股份涉嫌虚增利  围绕绿氢供应疏通产业链堵点
围绕绿氢供应疏通产业链堵点  创意闪耀,佳作频出!Kaadas
创意闪耀,佳作频出!Kaad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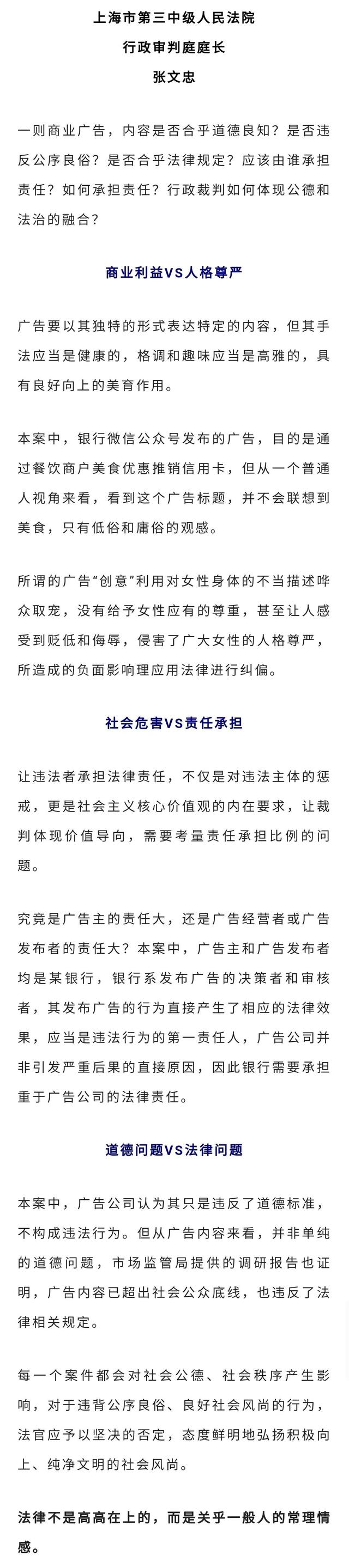 发布贬损女性广告被罚90万!
发布贬损女性广告被罚9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