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小玄儿
Part 1: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 )是谁?
这位导演的性格实在是太有趣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他经常在采访里说,自己是拍滑雪影片出身,进电影学院之前对电影史完全不了解——是个门外汉。
一方面他喜欢瑞典大师罗伊·安德森的电影,
一方面他受教于哥德堡电影学院老师的教诲
“Look into the core of the pain to be a human being.”
于是,鲁本·奥斯特伦德就从自己的生活出发,
开始摸索电影应该如何挖掘:“生而为人的痛苦”。
他先是拍摄了一个短片,关于自己的父母时隔21年后,第一次谈论两人离婚的始末。
鲁本·奥斯特伦德对这种,人们会本能的「闭口不谈」的事情特别敏感。
他特别想去追问,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开口谈论某些问题?
比如一夜情之后,两个成年人会如何对话?
比如和女朋友约会,如何讨论到底该谁买单?
鲁本·奥斯特伦德认为,如果他的电影能给到观众一个契机,
去谈论这些事情,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他把观众拉进电影故事的方式非常特别,
那就是制造一个典型的 Ruben Östlund 困境。
Part 2 Ruben Östlund Situation
以他最近的「男人困境三部曲」为例。
在《游客》中,是丈夫也是父亲的Thomas,
因为害怕雪崩而丢下了妻子和孩子,
事后却无法承认和面对自己的胆怯,最终彻底崩溃。
在《方形》中,艺术策展人 Christian
因为丢了钱包和手机,
向一整栋楼的居民散步恐吓信,
私生活的失控也导致了他在工作上的失职,
个人信誉和职业生涯尽失。
在《悲情三角》中,模特Carl先是被困在与女友的不对等关系中,
之后又面临了更大的生存困境。
也许是多年拍摄滑雪电影的经历,
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电影总是喜欢从「一场雪崩」开始。
首先,设定一个空间场景,
可以是雪山、度假村、艺术馆、游艇或小岛等等。
然后,让身处其中的角色,遇到一场意外,
可以是雪崩,丢钱包,沉船等等。
导致他们犯下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不大,
但是却有些丢人,至少是你不想在公开场合承认的那种。
鲁本·奥斯特伦德特别喜欢去探讨,现代人在道德困境下的反应。
也就是人在自私自利的本性,与维持社会身份和道德尊严之间的矛盾。
经典的「鲁本·奥斯特伦德困境」让会角色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是直接认错,也是他故事中的角色通常不会选择的解决方案。
另一种就是否认,故事中的男性角色通常会为了面子,
让一个「小雪球」越滚越大,发展成一个人的情感、家庭和职业危机。
最终,整部电影变成一场社会实验和人类观察,
通过把观众带入人物的困境之中,
引发大家去思考自己会如何反应。
鲁本·奥斯特伦德尤其对自己的生活圈层感兴趣,
正因为知道欧洲人不喜欢谈移民问题,
不想面对阶级差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他才一再的在电影里去挑战现代社会中的信任,
去刺破那些人人平等的谎言。
甚至用一整部电影,抓住中产阶级精英的小辫子不放,直到他们完全崩溃。
鲁本·奥斯特伦德说自己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Youtube Video,Google Image 和社会调查。
他说自己对一个生活中的问题感兴趣后,
就会在网上搜索,例如 Worst man cry 的视频。
在画电影分镜的时候,会到谷歌图片里找灵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会去看很多社会学研究资料。
看多了鲁本·奥斯特伦德的采访,
我觉得他本人就像他电影里的角色一样。
例如在谈到《悲情三角》的创作时,
他说自己就曾和身为时尚摄影师的妻子争论到底谁该为晚餐买单。
So, if you go the Hôtel Martinez (Cannes, France) and you look into the elevator shaft you probably will find a 50 euro bill there.
如果你去到戛纳的 Martinez 酒店,在电梯井里很有可能找到50欧元纸币。
在《游客》被瑞典选送奥斯卡角逐最佳外语片时,由于没有入围,他在酒店里哭到崩溃。
Part 3 空间、建筑与社会隐喻
让我们说回社会学研究,
这次重看鲁本·奥斯特伦德的三部电影,他选择的空间都非常有趣。
例如:《游客》最后的巴士,《悲情三角》中的游艇,
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出来其中对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比喻。
你可能甚至会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简单,
例如荒岛实验,把社会阶层倒置之类的。
这谁都想得到,但是就是这样的简单类比,
近些年不断地出现在金棕榈的电影里。
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提出了著名的「船喻」,
将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治理
比作指挥一艘在茫茫大海上颠簸航行的木船。
他将集体公民比作这艘木船的拥有者即船东,
船东是所有者,但是缺乏必备的航海知识;
喧嚣的政客是吵闹的水手;
而哲学家(哲人王)则是观星者兼掌舵人,
他知晓船的航向并熟练掌握着驾驭船只的「航海术」。
尽管水手们自夸掌握着这一技术并总是积极地向船东争取掌舵权,
甚至不惜动用酒精和毒品、并贬损作为掌舵人的哲学家,
但实际上他们一无所知。
借助这一隐喻,一个国家治理的现状显得通俗易懂。
这一隐喻,显然在《悲情三角》中被挪用。
只不过,导演似乎在其中另外添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的「大厦隐喻」。
这一空间隐喻将一个社会整体分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代表着文化与政治的权力结构,
对应的经济基础代表着生产方式与劳动关系。
上层建筑在影片中被简化为富商与贵族游客,
而中层则是中产阶级消费者,以及保证整个游艇正常运转的服务人员,
以领班为代表负责执行体制的规则,满足贵族乘客们的愿望,就算是船长也能不例外。(擦并不存在的船帆)
游艇的底层还住着水手、厨师和清洁工,
影片还特意强调了作为乘客的俄罗斯商富商,
由于没有见过引擎室的工作人员而发生的争执。
「大厦隐喻」在另一部金棕榈影片《寄生虫》中也尤为明显。
这些比喻对于我们来说,甚至已经不算是「隐喻」了。
更重要的是导演如何把这个比喻用影像和空间呈现出来。
《寄生虫》给人印象深刻的转折,
是一场暴雨带给不同居住环境的人,怎样天翻地覆的影响。
而《悲情三角》里我最喜欢的桥段,
是借用晕船和生理系统的崩溃,
让乘客们不再能伪装出体面的模样,
把他们打回原形,还原为人的样子,
在生存危机下被独孤、绝望和恐惧笼罩。
而清洁工们听着摇滚乐,彻夜打扫乘客们的污秽,
他们集体的工作形态,相互协作的效率,
与上层乘客们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悲情三角》里的阶级分化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比如二刷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次推开Carl的房门,
问他要不要客房服务的就是 Tolet Manager Abigail。
他们之间的一门之隔,也是是两个阶层之间,
默认地选择互不打扰,避免接触的生存法则。
一旦产生交集,也可能是毁灭性的。
例如 Carl 的投诉让水手丢掉了工作。
一旦 Abigail 有机会跃升社会阶层,
也有可能会对阻碍她的人产生杀意。
空间上的隔离只是电影的表层结构,
而导演要指向的是我们内心的阻隔,
只有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在回避问题,
才会想到为社会空间的固化做点什么。
Part 4 Ruben Östlund 的悲喜剧
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故事,
总是关于难以抉择的道德和生存困境,
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却看得乐在其中。
因为他太擅长把观众放在第三视角了,
在公共空间里比如《游客》里的清洁工,
《悲情三角》里的出租车司机等等。
在故事场景和私密空间里,
导演还特别喜欢设置小孩和宠物的在场,
制造一个严肃场景的同时,
却充满了戏剧化的气氛。
再加上巧妙地利用空间里的环境音,
例如《游客》里漫长的上山传动带一直发出诡异的声音,
就像这个正在被沉默和谎言肢解的家庭。
《方形》里的艺术装置,
不断地打断一夜情过后的男女对话。
而《悲情三角》租出车里的雨刷器,
制造着这对情侣之间的尴尬气氛。
还有那些一直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昆虫,
都是导演特意用后期特效创造出来的,
让观众产生【临场感】的元素。
最后,鲁本·奥斯特伦德说自己的电影很简单,
在一个空间(Space)里的,
一个群体(Group)中的个体,
如何试图保全自己的面子(Face)。
故事通常围绕着三个关键词
也就是讨论一个重要议题(Important),
关于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Sad),
深陷其中的人却略显滑稽(Funny)。
于是,就形成了这三部电影里的
三个男性角色(Tomas、Christian、Carl)
在《游客》获得成功后,
鲁本·奥斯特伦德说他早就想好了,
下一部电影《悲情三角》要搞个大的,
从时尚圈、到亿万游艇,再到无人荒岛。
并且他的下一部作品也确定了,
故事将发生在一架封闭的飞机上,
名片暂定为《娱乐系统暂停》。
相信你肯定也会想看看,
现代人会如何在飞机上度过
没有娱乐节目的十几个小时。
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拍摄电影之初,
就说自己一定要拍摄与观众互动的电影。
他和制片人 Erik Hemmendorff 在成立「平台 Plattform Produktion」 电影公司的时候,
更是扬言要做一个不撒谎的制作公司。
他一再地用电影去挑战观众们的底线,
讲述几个移民的孩子如何打劫中产阶级白人的小孩儿。
去展现一个家庭中男人的崩溃,
更是拿所有阶层的人来开玩笑,
把艺术圈和时尚圈的人都讽刺一遍。
很多时候,投资人们都认为这将是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最后一部影片了,
结果20多年来,他和最初的制片人一路搭档,拿了两个金棕榈!
这个当年的电影门外汉,没有理由不开心!
好啦,感谢你看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在大银幕二刷《悲情三角》,
以及回顾「男人困境三部曲」的感受。
欢迎分享你对影片和导演的看法。
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全球微头条丨新股首日 |
全球微头条丨新股首日 |  美联储激进加息对A股和港股
美联储激进加息对A股和港股  【5G商业赋能】AI加持,思特
【5G商业赋能】AI加持,思特  全球微资讯!高质量发展“五
全球微资讯!高质量发展“五  “AI四小龙”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龙”上市之路各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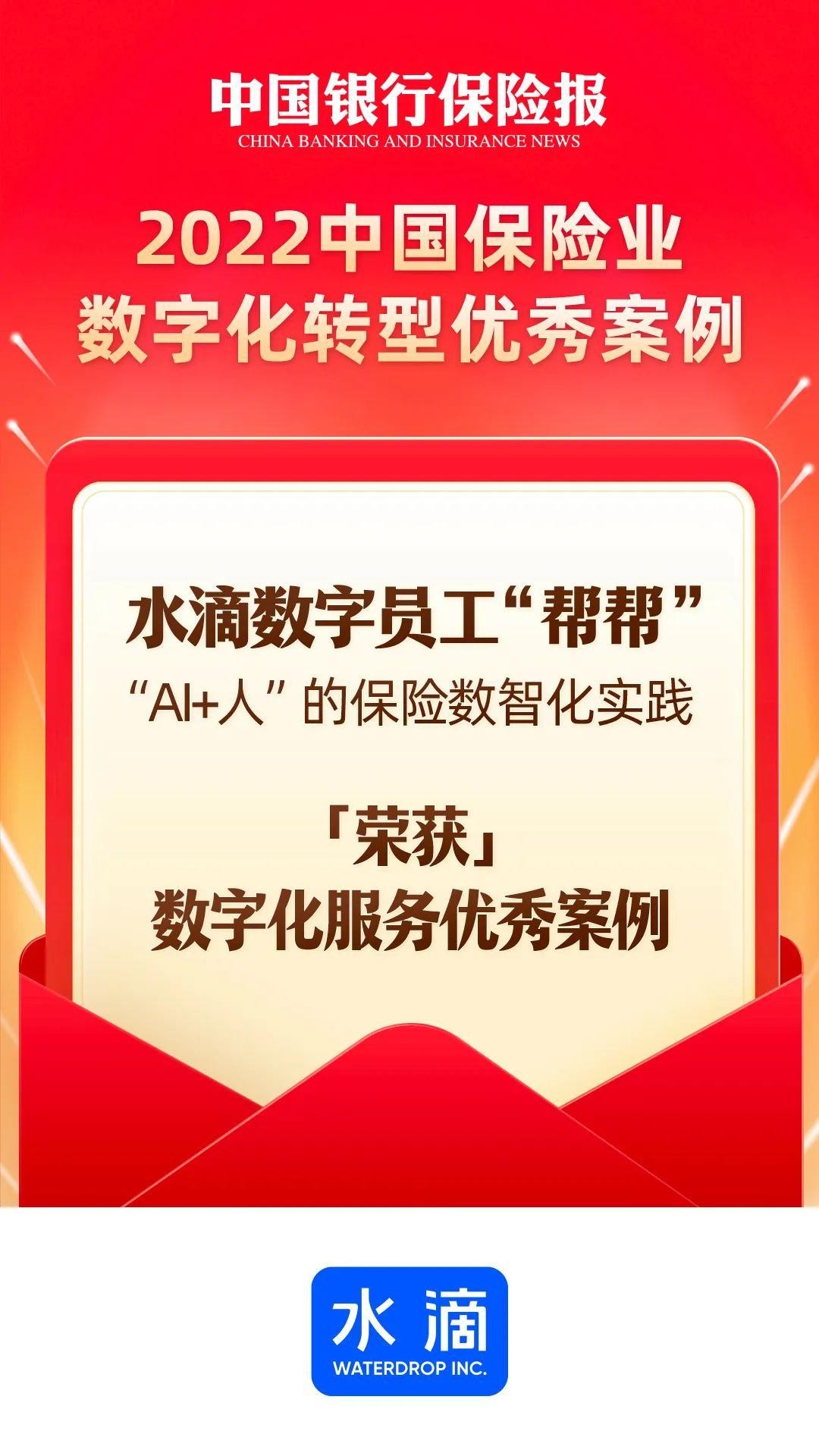 水滴公司荣获“2022中国保险
水滴公司荣获“2022中国保险  深圳坪山新能源车产业园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车产业园一期 



